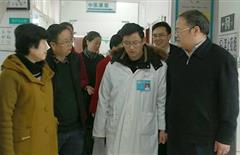孙次舟清军在四川的血腥罪行
发布时间:2018-09-26 17:59:18
发布时间:2018-09-26 17:59:18
孙次舟清军在四川的血腥罪行
张献忠失败前,川东、川南遭到明官军和地主武装的破坏,川北遭到“摇黄”和清军的破坏。到张献忠失败后,川西才被明军、清军、“摇黄”,特别是清军,轮番杀掠,这才彻底沦于残破。由于此后清军连续不断地向四川人民进攻近二十年,乃把整个四川搞到人口灭绝、城邑破碎、田野荒芜、虎狼纵横的地步。
从顺治四年(丁亥,1647)到顺治八年(辛卯,1651),有五年期间,是张献忠部属撤离四川,而明军和清军对垒,反复争夺四川城池的时期。清军和明军内部,也时有内讧,争城劫粮,涂炭人民。据《荒书》所记,顺治五年(戊子),“袁韬屯重庆寨山坪,残民复被杀戮,存者人又相食。”而这年,清兵“屯保宁、东至顺庆,西至中江县。自什邡县以西,叙州府以南,则杨展屯也。”《荒书》又说:“至南北用兵以来,北以保宁为大镇,中江、顺庆为边;南以嘉定为大镇,而成都为边。”成都既然作了明军的边垒,则当清军先之进攻杨展,以后进攻刘文秀,都是一个首先被反复争夺的城池。而在顺治五年(戊子)以前,成都就被清军彻底破坏了。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秋八月,献贼弃成都北去。”(《蜀乱》)“杨展前锋至保宁,大清兵入,展复引还。”“大清既诛献贼,令赵荣贵入成都”(《荒书》),成都便被清军和降军予以破坏。《荒书》记顺治四年(丁亥):“成都残民多逃雅州,采野菜而食,亦有流入土司者,死亡满路。尸才出,臂股之肉,少顷已为人割去,虽斩之不可止。是年春,大清李国英入成都,留张得胜守之,辟草莱而居。国英旋遂宁、潼川。”“白联芳……降大清,为成都都使司。诱得胜裨将张士聪、王材官为乱,夜杀得胜。……自得胜死,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按,清军入成都后造成的这种残破,《明史》列传都诬加到张献忠身上)杨展趁清军内讧,再度进入成都,“遣塘马四营,分镇成都四城”(《蜀乱》)。)顺治五年(戊子),“摇黄”武大定被清军围击,逃到川西,进入成都,“大饥困,差官投杨展求援。”这时成都已经空无所有,无法驻扎军队了。杨展最初还勉强“按月运粮以济之”,最后只得令武大定移营驻青神了。至于川北的保宁、顺庆二府,也被清军在几年内逐步破坏。《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载顺治七年《四川巡按张瑃揭帖》说:
“窃照川中见有保宁、顺庆二府,山多田少,……昔年生齿繁而虎狼息。自遭献逆‘摇黄’大乱,杀人如洗,遍地无烟。幸我大清恢靖三载,查报户口,业已百无二、三矣!方图培养生聚,渐望安康。奈频年以来,城市鞠为茂草,村畦尽变丛林,虎种滋生,日肆吞噬。……据顺庆府附郭南充县知县黄梦卜申称:原报招徕户口人丁五百零六名,虎噬二百二十八名,病死五十五名,见存二百二十三名。新招人丁七十四名,虎噬四十二名,见存三十二名。造册具申到职。……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远,尚不免于虎毒,而别属其何以堪耶?”
很明显,川北保、顺二府的“鞠为茂草,……虎种滋生”,是清军“恢靖三载”给造成的。
据我考察,清军是在顺治二年(1645年),便进入了四川(据《客滇述》、《荒书》乙酉年记事,及《蜀碧》卷四李国英条),接着在川北保宁建立了军事据点。先后统兵向四川进攻的大员,有豪格、鳌拜、吴三桂、墨尔很、李国翰和李国英、高民瞻等。直到康熙四年(l665年),把“西山十三家”全部打败为止,清兵在四川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才算基本停止。目前残存的清军在四川屠杀人民的血腥记录是这样的:
顺治三年(1646)进攻张献忠:“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一万二千二百余匹”(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三年进入成都:“赵荣贵于杨展退出成都后,以龙安降于肃王。王于是使固山檀太追贼党,而使赵荣贵入成都。先时,贼遁月余,杨展、曹勋等侦得之,于九月入成都。……如是者年余。时展等闻荣贵将至,议以成都难守,各引兵归。及荣贵至成都,见千里无烟,无所设施,亦还龙安。”(《蜀难叙略》)
顺治四年(1647)成都撤退:“明宗室朱容藩来寇,王帅(清兵)退屯保宁。成都守者亦驱残民千余北去,至绵州,复尽杀之。成都之人,竟无遗种。”(《鹿樵纪闻》)“(杨)展即遣杨荣芳、李一进、陈应荣、黄美,恢复成都。……十一月,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客滇述》)
顺治四年围茂州:“清将赵荣贵围朱化龙于茂州。化龙固守三日(按,“日”应作“月”),食尽而陷。荣贵复叛清,与化龙盟而去,屯于龙安。方茂州围时,男子肉每斤七钱,女子肉每斤八钱,冢中枯骨皆掘出为屑以食焉。”(《客滇述》)
顺治六年(1649)进攻中江、潼川、射洪:“叛将王基城旧部林时泰等,前杀基城来降,……令分防中江、潼川。射洪等处。……据城噪叛。……臣遣副将曾纯忠……等,分兵攻剿,斩获无算”(王先谦:《东华录》)。李国英原奏报说:“当阵杀死叛贼不计其数,活擒叛逆五百余名,一并斩讫。获得马骡捌拾伍匹,……妇女五十五口,俱经留营。”(《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
顺治六年进攻邻水、大竹:“镇臣卢光祖等,率兵往剿。鏖战七昼夜,……二逆先后伏诛,余党悉除。邻、大二县,俱入版图。”(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七年(1650)进攻达东山寨;“上寨斩杀逆贼百十余人,跳岩跌死者无数。共捉获男、妇四十一名,黄水牛九只,大小猪二十只。……十一名发市曹枭首传示。……所获妇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赏有功。”(《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李国英揭贴》)
顺治八年(1651)令吴三桂进兵四川:“命平西王吴三桂与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率师征四川。”(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九年(1652)保宁防守战:“八月,(刘)文秀率众由永宁趋叙府,本朝守将马化豹等欲俟其至城下击灭之。须臾,文秀拥诸攻具登城,被杀者山积于城下,犹不能克。后城门为象所坏,文秀遂得入。……是日,(白)文选亦取重庆。……文秀乘势率众数万至保宁……攻城。我兵迎战于龙盘山下。良久,文秀大败,遁者又阻于河,遂全军覆没。惟文秀与张黑神等数百人,赖浮象而免。”(《蜀难叙略》)“九月,文秀与张先璧至保宁。大清兵击败之,杀千人,生擒数千人,皆杀之。文秀、光璧以数千残卒,遁归贵州。”(《荒书》)“吴三桂、李国翰奏:巨憝孙可望遣伪抚南王、伪将军王复臣等,率马步五万,入犯西安。巨等退师保宁,为决战固守之计。……贼众大溃,擒斩复臣(王复臣第一次被斩!)及伪将军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获伪印、象、马、器械无算。”(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十四年(1657)进攻嘉州:“平西工吴三桂率兵破嘉州城,生擒伪总兵龙名扬,招降……四川三州十六县。击败伪抚南王刘文秀马步兵,斩伪将军王复臣(王夏臣第二次被斩!)、总兵王之俊等,获金印及象马等物甚多。”(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十五年(1658)进攻开州:“吴三桂等奏:臣等收复重庆,即统军进发。……有伪总兵梁杰英等,拥贼三千有余,屯开州拒守。我兵奋勇分击,贼大败,阵斩二千有余,获其象马器械,遂克开州。”(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十六年(1659)防守重庆,进攻成都:“诸逆一十三家,……力图重庆,水陆环攻一十五日。……协心战守,杀死逆孽,飘落江水者,不计其数”(《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李国英揭贴》“巡抚高民瞻……进取成都,……追至新津河,阵斩及溺死无算。”(王先谦:《东华录》。李国英原奏,载《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
康熙二年(1663)三省分路进攻“西山十三家”:湖广提督董学礼奏,前奉命会剿湖广西山巨寇李来亨、马腾霄、党守素等,……统领官兵三万人,凿山开道,……进至李家店。遇贼兵万余人,各路奋击,斩馘过半。……又别遣夷陵镇将恢复归州(今湖北姊归)、巴东、巫山等处,直达夔州。”陕西总督白如梅奏,提督王一正,率兴安总兵官于奋起……进剿逆贼郝摇旗。至房县横水地方,伪罗军门将万余人拒战,大败之,杀贼兵无算。生擒一百七十三人,徇于军。”“四川总督李国英奏:进剿昌宁(即大宁,今巫溪县),直捣逆巢,渠魁袁宗第乘夜遁去。当阵杀死伪总兵以下六十员。”(王先谦《东华录》)
康熙三年(1664)打败“西山十三家”:“四川总督李国英等奏:蜀中巨寇刘二虎、郝摇旗、袁宗第,抗抚负固。……师次陈家坡,逼近贼巢,满、汉兵奋勇剿杀,贼遁入天池寨。杜敏等统兵进剿,刘二虎势穷自缢,郝摇旗、袁宗第夜遁。杜敏等复追至黄草坪,大败贼众,擒郝摇旗、袁宗第,并伪王朱宗蒗等。数万巨寇,一朝扫平,无一漏网。”“湖广总督张长庚奏,……合剿西山巨逆,郝摇旗、刘汝魁等,业经授首。独李来亨拥众茅麓山(湖北兴山县西北七十里),最为险峻。官兵昼夜环攻,贼势穷迫,其党陆续下寨归降。八月五日,李来亨全家自缢,举火焚巢。官兵搜剿余党,楚寇荡平。”(王先谦:《东华录》)“刘体纯、郝永忠辈合数万众于八月二十四日攻巫山县甚急,凡八昼夜。九月,大清兵出战,体纯等败走,永忠退屯大宁。……己而大清将军自陕西率兵至四川。十二月,大清兵入陈家坡,再夺老木孔,体纯自缢,举室焚死。大清乘胜以进,至黄草坪,永忠、宗第皆获。惟李来亨居茹茆麓山寨,高险难攻,湖广、四川兵围之。……甲辰(康熙三年)六月十五日,来亨出围国英营垒。既破而败。……八月初五日,(来亨)焚其妻子而自缢。茆麓破,获数千人,皆杀之。惟留妇女,散给营伍。……李、张二贼之余,至是尽矣。”(《荒书》)
根据以上清军进攻四川的残存资料,可以看出清军屠杀四川人民的惨重。清军的掠杀规律是:进攻时,拼命斩杀,俘获的丁壮,一概杀死;俘获的妇女、小儿、牛只、器物,则官、兵坐地分赃。玫下城池、山寨时,是要抢光、杀光,必使荡然无余而后已;放弃城池时,便把老百姓全部掳走,有时在半路上“复尽杀之”。象这样的反复攻杀,或“竟无遗种”,或“斩获无算”,或“余党悉除”,或“无一漏网”,一直延续了二十年没有停刀,整个四川,焉得不千里荒凉,人烟灭绝呢?
顺治十五年(1658),李国英正在调集“秦、蜀、楚三省大兵”会攻“西山十三家”时节,有一位做李国英幕僚的明阆(即阆中)庠生刘达,曾奉命往西宁口外购买战马,解到重庆。他在回川途中,看到川东北一带被“旗兵”破坏杀掠,不堪入目,不由义愤填胸,坚决向李国英请假返里。他给李国英写信道:
“曩出极塞,办买战马。……已而取道邠、凉,道经孔、雒,返乎三巴。见夫尸体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异,宛如隔世。……辄溉然太息!旋当枕石漱流,与老农老圃,课雨谋晴,富贵功名,讵我所知哉!”(《滟滪囊》卷四)
从刘达这封书信,可以看到清军屠杀四川人民的一幅缩影。这些血腥的罪行与张献忠又有什么干系呢?欧阳直《蜀乱》在叙述完了清军“攻剿夔东刘、李、党、郝、塔等十三家”后,总束前文说:
“自此,东、西、南三川,全归清,蜀乱暂定矣!自乙酉(顺治二年)以迄戊、巳(戊戌、巳亥,即顺治十五年与十六年),计九府一百二十州县,惟遵义、黎州、武隆(故治在今涪陵县东南)等处,免于屠戮。上南一带(嘉定),稍有孑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并无人种。且田地荒废,食尽粮空。未经‘大剿’地方,或有险远山寨,间有逃出三、五残黎。初则采芹挖蕨,继则食野草,剥树皮。草木俱尽,而人遇且相食矣!”
很明显这是清军长期向四川人民进行“大剿”,才弄到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田地荒废,食尽粮空”的地步。欧阳直已说出了清初“屠蜀”的真象。
在清军中,投降的汉军也和“旗兵”一样是残虐四川人民的。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二说:
“(吴)三桂镇蜀,虐使蜀人,蜀人咸貳。尽夺献忠将士子女,日置歌舞,诸将恨刺骨。……献忠所部,共推平东将军孙可望为主,潜勒两川散亡诸部曲,合兵袭成都。……三桂大败,弃成都东走。可望逐之,三桂且战且走,两川兵尽起攻本朝之戍守者。三桂仅得反汉中,可望遂踞两川。”
《明季稗史初编》《平西王吴三桂传》说:
“文秀善抚士卒,多乐为死。蜀入闻其至,所在响应。重庆、叙州诸郡邑为三桂所克者,次弟失陷。”
张献忠部属孙可望、刘文秀之能够反攻四川,打退吴三桂,就因为清兵和投降汉军的残民,而张献忠部属却是深为四川人民所拥护所支持的。《滟滪囊》卷四记康熙元年,“吴三桂移镇云南,家属道经四川,年余络绎不绝。船只夫役,供应浩繁,民疲于奔命。……民人逃匿,不获耕耘。”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吴三桂的侵害人民,尚且如此,若在军事行动期间,其残暴更可想见。
清政府自康熙四年对四川人民的屠杀暂告停止之后,曾用“鼓励招垦之法”(《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户部题本》),招徕他省人民到四川垦荒,企图借此略求恢复生产,增加赋税收入。但四川没有平静多久,到康熙十三年(1674),因“撤藩”之故,吴三桂和清朝发生决裂,吴三桂部属王屏藩强据了四川。双方为了争夺四川的地盘,进行了七年的血战。四川的残余和新迁来的少数人民,又大部分作了双方刀下之鬼。
玄烨调兵遣将,要向四川王屏藩、吴之茂等进攻。利用汉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把已经进攻到陕,甘间的王屏藩军打回四川。双方在汉中和川陕边界对峙了几年。清军借口转运困难,粮饷匮乏;又借口北京地震,“房屋倾坏,……人各怀内顾之忧”,请求暂缓进攻。玄烨除严令进军外,在康熙十八年十一月,下了就地“打粮”的“上谕”。《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八说:
“上谕户、兵二部:前据大将军等疏称,王屏藩诸贼,于汉中兴安诸处,拥众数万,坚定抗拒。以此推之,必广储粮饷,为数年之备。今我大兵,骤入恢复之也,贼所聚粮,必已多得。……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俾进蜀官兵,不误支给。……诸将军、大臣等,俱宜殚心储备,所获汉中诸处钱陵米谷,节省支用,副朕灭寇安民至意。此后所至之地,惟宜以此为急务。”
这纸冠冕堂皇的“上谕”,就是暗示进攻四川的官兵,只要能够拚命打进四川,所到之处,不管城市或乡村,准许大肆抢幼,尽量搜索财物。表面上说:“副朕灭寇安民至意”,实质上,是以牺牲四川人民的生命财产去引诱这一群虎狼将兵贪财忘生地拼命向四川进攻。这完全是明官军“扫粮”政策的扩展。玄烨又敕谕张勇、王进宝等四汉将,规定:“官兵前进,则满洲大兵,亦即相继进剿。”于是汉军在前,旗兵后继,到康熙十九年(1680)一月,已经由广元、保宁而攻下了成都。可是四川人民乃大受涂炭。先被汉军杀戮搜刮一番,紧跟着旗兵又来抢掠一场,诚如李瑨《平贼碑》所说:“甲寅(康熙十三年)之岁,逆藩煽乱,……全川陷失,……士民其瘵。渠邑界在东陲,实当孔道,兵篦寇梳,受祸尤烈。”(见《片石齐文集》)四川人民就在“兵篦寇梳”的情况下,被这群虎狼强盗抢光、杀光了。
清初的官僚,都知道掩盖自身罪恶的办法,把破坏四川的责任,诬加到张献忠身上。但从他们的四川纪行中(多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仍能看出四川逐步破坏的情形,和破坏逐步加深的程度。
康熙九年(1670),王澐随蔡毓荣入蜀安辑地方,他在《蜀游纪略》中说:“经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观盐井。……旁有废井,乃献贼所塞。他邑废井甚多,修复者十未及一。问火井,闻在富顺云。”但到吴三桂战乱后,陈奕禧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押运饷银入川(陈仅是县丞一类小官,偶尔还说几句真话),他在《益州于役记》中说:“盐亭、南部、阆中、射洪,皆有盐井,……惟南部多至五十二井。盐亭十六,为乱兵所塞,止存其一。”陈奕禧说破坏盐井的是“乱兵”,而王澐却推到二十多年前的张献忠身上,显然是故意栽赃的。王澐入川所见,成都破坏的最凶,只有嘉定还有完整的房舍。他说:
“成都,……官民庐舍,劫火一空。蔡公至,馆于棘园,即蜀王宫也。……惟有重城,馆舍皆草创。……又至青羊宫,楼观焕然,时贤所重构也。登楼四望,……阡陌宛然,溪流清驶,人烟久绝,尽成汙莱,山麋野豕,交迹其中。野外高丘累累,……城中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矣!(清政府由陕西招徕的)”
“至嘉州,……州治未被兵残,庐舍完整,为仅见云。”
康熙十一年(1672),王士祯典试入川,沿途所见,荒凉不堪。王在《蜀道驿程记》说:
“(闰七月)十三日,……次宁羌州。州在乱山中,无城堞。……明末流寇小红狼据之,又经献贼之乱,城郭为墟。”
“十四日,……二鼓抵黄坝驿。……夜闻呼噪声,询之,云麋多食稼,农夫野宿驱之故耳!”
“十六日,未午次广元县。……自宁羌至此,荒残凋瘵之状,不忍覩。闻近有旨招集流移,宽其徭赋,募民入蜀者,得拜官。”
“二十四日,午次盐亭县。……行十五里,次秋林驿,在深箐中。目前种种,如地狱变相。……人家十余,结茅竹在箐中。土人云,蛇虎虽多,与人无害。”
“二十六日,……哺抵建宁驿。竟日出没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结伴始敢行。”
“二十七日,……自潼川西来,山险稍平,然泥淖特甚。……弥望百里,田在草间。午后次中江县。……县颓废甚于潼川,境内人户才三十余家。”
“二十九日,……次汉州。……城中石表,咫尺相望,想见盛时。而城堞室庐,鞠为茂草矣。”
“八月,……初三日,……午抵成都府。”
“九月二十五日,发成都府,……次双流县,县已废入新津。……入城,即颓墉废堑,虎迹纵横。”
“二十八日,……出眉州西行。……弥望荒原,风雨如晦,数十里无饮烟,最为荒阒。”
“二十九日,……午次夹江县,嘉定州界。……自巴阆走成都至眉,千余里名都大邑,鞠为茂草。”
王士祯沿途所见的凋残情况是:川北自宁羌到广元,破坏的最凶,“城郭为墟”,居民稀少,“麋多食稼”,“荒残凋瘵之状,不忍睹”。自保宁经成都到眉州,“干余里名都大邑,鞠为茂草”,“田在草间”,城内“虎迹纵横”。可是四川又遭受了清军和王屏藩等七年战祸,到康熙十九年才算基本结束。所以康熙二十一年(1682)陈奕禧运饷银到四川,二十二年方象瑛典试到四川,他俩沿途所见到的情景,更加凄凉了。陈奕禧《益州于役记》说:
“(十月)四日,……至宁羌州,入北门,四郭皆荒草,缚柴为城门,刺史与城隍同衙。”
“十三日,十五里虎跳驿。烟火百家,……颇盛于县。”
“十五日,晤阆中令。……舍舟登陆,以民稀夫少,末得行。”
“十八日(按,陈在阆中等民伕数日),渡嘉陵江,稍南上锦屏山。……今逢变乱,古木尽遭逆兵戕斫,无复佳胜。”
“廿日,渡嘉陵江而南,……高地低田,兵余仅见耕耨。”
“廿一日,……十里柳边驿,宿馆舍。自入栈来,州邑皆荒残,无复烟火。”
“廿三日,……十五里紫荆铺小尖。岩阿群鹿,大者如马,往来于荒田中,止息甚闲。……廿五里盐亭县,宿店。”
“二十四日,……十里庙垭,见虎。……十里秋林归驿,宿店。……终夕群虎逐鹿,呜声绕床不绝。”
“二十五日,……十五里桃花溪。……土地肥厚,人民不存,鞠为蓬茆。”
方象瑛《使蜀日记》说:
“八月,……十七日,是夕泊广元县。……二十日,经苍溪县,……午余抵保宁府。二十二日,渡阆水复陆行。次龙山驿,舍宇颓废。……夜趋柳边驿,不及宿。小猴牙草舍索米,不得,取干粮给从人,燃薪达旦。……二十三日,次柳边驿,颇多居民。……二十四日,由灵山铺至盐亭县。川北自保宁以下,旧称陆海,明末张献忠屠戮最惨,城廓村镇尽毁。田野荒芜,人民死徙,处处皆然。……二十六日,抵潼川州。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九月一日,次汉州,抵新都县,皆名区。乱后中衢茅屋数十家,余皆茂州(指羌人。今设茂汶羌族自治县),虎迹遍街巷。”
当王士祯入蜀时节,在亭子口、阆中、盐亭等城镇,还偶见恢复景象:“亭子夹岸居民数百家,有良田沃野。”“阆中人氏城郭,在川北诸郡,差为完好。”“盐亭县……城堞已毁,居民尚数百家。”但到陈奕禧、方象瑛入蜀时,川北个别地区的恢复情况,已行消失。王士祯在亭子口见到“居民数百家”,盐亭县“居民尚数百家”,可是陈奕禧在虎跳驿见到“烟火百家”,便认为很难得了。以王士祯时“人民城郭”“差为完好”的阆中,到陈奕禧来时,竟变成“民稀夫少”,等了几天,才拉齐伕子。一般地看来,残破的程度,又加深了一步。象潼川:王士祯所见,是“弥望百里,田在草间。”但方象瑛所见,是“沃野千里,尽荒芜,田中树木如拱”。田中荒草竟变成树木了!象汉州:王士祯所见,是“城堞室庐,鞠为茂草。”但陈奕禧所见,是“城内外皆林莽,成虎狼之窟。”象成都:康熙九年王澐所见,尚有“棘园”,“馆舍皆新创”,郊外田地“山麋野豕,交迹其中”,“青羊宫,楼观焕然。”但方象瑛所见,则“无使院”,“亦无院署,僦民宅以居”,城内“虎狼且攫人”,青羊官“旧极壮丽,今圮。”请问,象这样地把四川搞得愈来愈荒凉,人烟愈来愈稀少,变成荒草丛树,虎狼横行的世界,究竟是谁的罪恶呢?
陈奕禧说:中江县“城大而荒,民四十家,赋六金。”方象瑛说:“额赋,大县不过五十金,或一、二十金,甚至四、五金。人亡土芜,目中所未见,招徕生聚,故未易也。”徐乾学在《送姚佥宪抚蜀序》(《憺园文集》卷二十三)和方象瑛一样,把四川的“数被兵革,地荒民流”的惨祸,推到张献忠和吴三桂身上。但戴名世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写的《李县圃唱和诗序》说:“自明之末以来,而蜀已非前日之蜀矣!使子美、务观见之,当如何叹息?”(《南山集》)他言外有物,却不敢明白说出这残害四川的罪首。川东传教神甫古洛东根据清初四川传教记录,在所著《圣教入川记》中写道:
“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一时末能设官治理。彼时川人不甘服旗 *** 下者,逃往他处,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年。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顺治十七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己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康熙六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康熙二十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哀哉川民,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幸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匪党盗寇,悉为殄灭。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