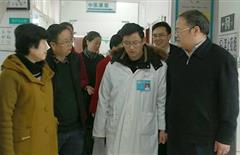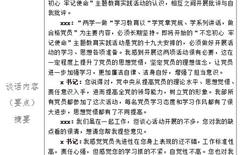冰心代表作散文:每逢佳节
发布时间:2020-05-08 03:54:10
发布时间:2020-05-08 03:54:10
冰心代表作散文:每逢佳节
修养的花儿在寂静中开过去了,成功的果子便要在光明里结实;下面是有冰心代表作散文,欢迎参阅。 冰心代表作散文:每逢佳节 唐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同东兄弟》这首诗,一千多年来脍炙人口,每逢 佳节,在乡的游子,谁不在心里低徊地背诵着: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其实,在秋高气爽的风光里,在满眼黄花红叶的山头,饮着菊花酒,插着茱 萸的兄弟们,也更会忆起“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王维,他们并户站在山上遥望天 涯,也会不约而同地怅忆着异乡的游子,恨不得这时也有他在内,和大家一起度 过这欢乐的时光。 我深深知道这种情绪,因为每逢国庆,我都会极其深切地想到我们海外的亲 人。在新秋的爽风和微温的朝阳下,我登上天安门前的观礼台,迎面就看到排成 一长列的军乐队,灿白的制服和金黄的乐器,在朝阳下闪光,还有一眼望不尽的, 草绿的,白色的一方方的象用刀裁出来各种军队的整齐行列,他们的后面是花枝 招展的象一大片花畦的少年儿童的队伍,太远了,听不见他们的笑语,但看万头 攒动的样子,就知道他们在欢悦地说个不停……这一切,从礼炮放过的两个钟头, 直到我们伟大的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贵宾们,在天安门城楼上从东到西向我 们挥帽招手时为止,我的心一直在想着许许多多现在在国外的男女老幼的脸,我 忆起他们恳挚的直盯在你脸上的眼光,他们的倾听着你谈话的神情,他们的从车 窗外伸进来的滚热的手,他们不断起伏的在我们车外唱的高亢的《歌唱祖国》的 歌声……我想,这时候,在全地球,不知道有几千万颗的心,向日葵似地转向着 天安门,而在天安门上,和天安门的周围---这周围扩大到祖国国境的边界------- 更不知道有几亿万颗心,也正想念着国外的亲人啊! 观礼台前涌过浩荡的彩旗的海,欢呼的声音象雄壮的波涛一般的起落,我的 心思随着这涛声飘到印度的孟买,我看到一个老人清癯的布满皱纹的笑脸,他出 国的年头和我出生的年纪差不多一样长!他是那般亲热地、颤巍巍地跟在我们前 后,不住地问长问短,又喜悦,又惊奇,两行激动的热泪,沿着眼角皱纹,一直 流下双颊…… 我的心思,飘到英国的利物浦,在一个四壁画满中国风景,屋顶挂着中国宫 灯的饭店里,那一对热情的店主东夫妇,斟上一杯又一杯的浓郁的酒,欢祝祖国 万岁,祖国人民万岁,勉强我们一杯一杯地喝干。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使得他 们三十多年来抛乡离井,异乡糊口的生活,突然增加了光彩,看见了来访的亲人, 更使他们兴奋,他们的眼里、身上,涌溢着如海的深情……谁道“西出阳关无故 人”?我们虽是不会喝酒的人,那时是“十觞亦不醉”地痛饮了下去…… 我的心思,飘到缅甸的仰光,码头上长行的献花的孩子,向着我们扑来。这 一群华侨儿童,打扮得出水芙蓉一般的皎洁秀丽,短裤短裙,露出肥胖的小腿, 复额的黑发下闪烁着欢喜的眼光。他们献过花,便挽在我们的臂上,紧紧地跟着 我们走,我笑问他们:“你们认得我么?怎么跟我们这么亲热呵?”他们天真地 笑着仰头说:“为什么怕生呢,你们是我们的亲人呵!”他们说的普通话,是那 么清脆,那么正确,“亲人”这两个字,流到我们的耳朵里,把我们的心都融化 了…… 我的心思,飘到日本的镰仓,这一所庭园,经过一场春雨,纤草绿得象一张 绒毯,几树不知名的浓红的花,在远远的亭子边开着。我住的这间“茶室”,两 面都是大玻璃窗,透亮得象金鱼缸一样,室内一张方方的短几,一个大大的火盆, 转着火盆抱膝坐着几个华侨青年。这几个青年,从我们到日本访问起就一直陪着 我们,但是我们忙着访问,他们忙着工作,一直没有畅谈过,现在我们到镰仓来 休息了,他们决不放过这个机会,但是他们又怕我们劳累,在纸门外你推我让, 终于叩门进来了……我们转着火盆,谈着祖国建设,谈着世界和平,谈着中日友 好,谈着他们各人的生活,志愿……谈得那样热烈,那样真挚,直谈到灯上夜阑, 炉火拨了又拨,添了又添,若不是有人来催,他们还恋恋不肯离去……。 我的心思,飘过异国的许多口岸,熨贴着各处各地在异乡作客的亲人。他们 和他们的祖先都是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被从前的黑暗政治所压迫,咬着牙飘洋 过海,到远离祖国的地方,靠着自己坚强的双手,经过千辛万苦,立业成家。在 祖国悲惨黑暗的年头,他们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岁时节庆,怅望故乡,也只 有魂销肠断;然而他们并不灰心,一面竭力地从各方面辅助祖国自由独立的事业, 一面和当地人民合作友好,鼓着勇气生活下去。英雄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十二 年之中,不但站得稳,而且站得高,成了保卫世界和平的一面鲜红的旗帜。如今, 我们海外的亲人,每逢佳节,不是低徊抑郁地思乡,而是欢欣鼓舞地悬想着腾光 溢彩的天安门。但是,他们应该会想到,在天安门上面和周围,也有无数颗火热 的心在想着他们,交叉的亿万颗心,在同一节奏里剧烈地跳动。这种音乐,和我 们的社会主义的祖国一样,是崭新的,它鼓舞着我们,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 隔着海洋,一同为祖国建设和世界和平尽上我们最大的力量! 冰心代表作散文: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 昨天下午四点钟,放了学回家,一进门来,看见庭院里数十盆的菊花,都开得如云似锦 ,花台里的落叶却堆满了,便放下书籍,拿起灌壶来,将菊花挨次的都浇了,又拿了扫帚, 一下一下的慢慢去扫那落叶。父亲和母亲都坐在廊子上,一边看着我扫地,一边闲谈。 忽然仆人从外院走进来,递给我一封信,是一位旧同学寄给我的,拆开一看,内中有一 段话,提到我做小说的事情,他说“从《晨报》上读尊著小说数篇,极好,但何苦多作悲观 语,令人读之,觉满纸秋声也。”我笑了一笑,便递给母亲,父亲也走近前来,一同看这封 信。母亲看完了,便对我说,“他说得极是,你所做的小说,总带些悲惨,叫人看着心里不 好过,你这样小小的年纪,不应该学这个样子,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文字,和他的前途,是很 有关系的。”父亲点一点头也说道,“我倒不是说什么忌讳,只怕多做这种文字,思想不免 渐渐的趋到消极一方面去,你平日的壮志,终久要销磨的。” 我笑着辩道:“我并没有说我自己,都说的是别人,难道和我有什么影响。”母亲也笑 着说道,“难道这文字不是你做的,你何必强辩。”我便忍着笑低下头去,仍去扫那落叶。 五点钟以后,父亲出门去了,母亲也进到屋子里去。只有我一个人站到廊子上,对着菊 花,因为细想父亲和母亲的话,不觉凝了一会子神,抬起头来,只见淡淡的云片,拥着半轮 明月,从落叶萧疏的树隙里,射将过来,一阵一阵的暮鸦咿咿哑哑的掠月南飞,院子里的菊 花,与初生的月影相掩映,越显得十分幽媚,好像是一幅绝妙的秋景图。 我的书斋窗前,常常不断的栽着花草,庭院里是最幽静不过的。屋子以外,四围都是空 地和人家的园林,参天的树影,如同曲曲屏山。我每日放学归来,多半要坐在窗下书案旁边 ,领略那“天然之美”,去疏散我的脑筋。就是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也是帘卷西风,夜凉 如水,满庭花影,消瘦不堪……我总觉得一个人所做的文字和眼前的景物,是很有关系的, 并且小说里头,碰着写景的时候,如果要摹写那清幽的境界,就免不了用许多冷涩的字眼, 才能形容得出,我每次做小说,因为写景的关系,和我眼前接触的影响,或不免带些悲凉的 色彩,这倒不必讳言的。至于悲观两个字,我自问实在不敢承认呵。 再进一步来说,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 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 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何况旧社会旧家庭里,许多真情实事,还有 比我所说的悲惨到十倍的呢。我记得前些日子,在《国民公报》的《寸铁》栏中,看见某君 论我所做的小说,大意说: 独憔悴》小说,便对我痛恨旧家庭习惯的不良……我说只晓得痛恨,是没有益处的,总 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这“痛恨”和“努力改良”,便是我做小说所要得的结果了。这样便是借着“消极的文 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了。 就使于我个人的前途上,真个有什么影响,我也是情愿去领受的,何况决不至于如此呢。 但是宇宙之内,却不能够只有“秋肃”,没有“春温”,我的文字上,既然都是“苦雨 凄风”,也应当有个“柳明花笑”。 不日我想作一篇乐观的小说,省得我的父母和朋友,都虑我的精神渐渐趋到消极方面去 。方才所说的,就算是我的一种预约罢了。 冰心代表作散文:小桔灯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 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登、登、登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 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 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 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 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桔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桔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 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桔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桔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