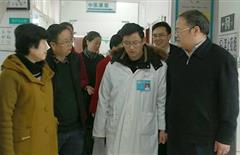自愿捐献器官有多难
发布时间:2020-08-03 10:10:01
发布时间:2020-08-03 10:10:01
自愿捐献器官有多难
首席记者|杨 江
【摘 要】器官自愿捐献与移植系统之于中国,就像一个移植器官之于新的身体,在中国运转还要经历“排异”关。2015年1月1日起,中国把停止利用死囚器官开展器官移植手术,作为最新的目标,来自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将成为我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最主要器官来源。
【期刊名称】新民周刊
【年(卷),期】2015(000)014
【总页数】5
【关键词】移植器官;器官移植;中国;手术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把停止利用死囚器官开展器官移植手术,作为最新的目标,来自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将成为我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最主要器官来源。
中国器官自愿捐献事业起步晚,但进步明显,自愿捐赠器官的数量在2014年出现了猛增,全年捐献达到1400多例,上海市截至2015年3月20日,共产生自愿捐献79例。数据显示,2013年时上海市自愿器官捐献还只有5例,但到了2014年跃升至55例,今年截至3月底已经有19例,上海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汤兆祥预计,2015年的捐献数量将超过2014年。
其实,论数字,上海的器官自愿捐献数在全国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与其城市的地位不匹配,远远落后于浙江、广东等地。但考量中国的器官捐献与分配工作,却不能绕开上海。
中国器官自愿捐献与移植体系参考了国外很多好的经验,但由于建立不久,再加上中国环境复杂,新的系统需要更多的完善。器官自愿捐献与移植系统之于中国,就像一个移植器官之于新的身体,在中国运转还要经历“排异”关。
器官紧缺加剧
上海仁济医院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器官移植医院,肝脏外科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该科科主任兼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成员夏强告诉《新民周刊》,我国器官移植政策的变化确实给医院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排队现象在加剧”。
而这样的状况在上海的长征医院、中山医院都同样存在,中山医院泌尿科主任医师、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同玉说,该院患者排队等待器官平均需要5年,而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的医生张雷反映该院现在排队等待器官的病人至少四五百人,一些病人已经等待了十多年。
我国2010年开始推动器官捐献工作,当年3月,在天津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随后一些地区开始部署器官自愿捐献工作,但上海由于一些特殊原因直到2011年底才逐渐开始推动,因此较浙江、广东等地区而言,上海真正的起步工作比较晚。
对于死囚器官利用的问题,目前争议较大,典型的观点如第二军医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华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所持的那样,认为死囚也有权利自愿捐献,可以纳入自愿捐献体系,只要法制化,公开透明即可,不宜一刀切叫停。
张雷估计,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2年以后医院的移植手术量能够恢复到2002年左右的水平,当时,全国器官移植手术量约1万例,“2013年全国自愿捐献700例,去年翻番到了1400例,但这样的推测是建立在现有体系健康蓬勃发展的基础上,OPO现在看来发展不错,但明后年会否继续保持这种良好的态势,是未知的,而且发展还可能会遇到瓶颈期。”
来自长征医院的数据反映,较之死囚器官比例的不断下降,这几年,来自DCD(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捐献快速上升,亲属活体捐献稳步上升,2013年DCD车祸捐献的比例就已超过了死囚的捐献,2014年,长征医院开展了154例肾移植手术,有60例左右来自DCD,还有一部分是亲属捐献。
何时才能弥补缺口难以判断。病人的数量是在上升的,自愿捐献的上升幅度没有死囚器官利用下降的幅度大,差距肯定拉得越来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家医院只能根据自身的医疗特点想办法尽量弥补缺口。
夏强认为,以仁济医院为例,现在能做的就是加强器官捐献的动员力度,提高公民自愿捐献率,以及开展亲属间的活体移植。
运动员兼裁判员?
“画虎不能画成犬”,这是中山医院泌尿科主任医师朱同玉的提醒。“一般一座城市有一个OPO就够了。”根据他的了解,美国一般一个州只设一个OPO,而且这个OPO不隶属于任何医院,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捐献者到OPO捐献器官后,分配到全州所有医院,分配过程接受社会的监督。
“OPO一定要与移植医院脱钩,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是不合适的。技术上可以依靠医院,但管理上不能属于医院。”朱同玉说。
目前我国在各个开展移植手术的医院内设置OPO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接受相关部门与卫生部门的监管,但工作人员与日常运行管理人员则来自医院内部。
就分配而言,朱同玉透露,目前尚未完全实现全国分配的理想状态,“有些医院一年能分配到两百个器官,而有些医院却少得可怜?现在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移植手术量与医院整体的技术水平关系不大,主要看医院自己OPO的工作情况,这与国际公认的分配方式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这样的现状不利于患者。。这样的现状不利于患者。我也希望我们能迅速跨过OPO发展的初级阶段,逐步与国际接轨”。
实际情况是,器官的全国分配还停留在理论上,操作中遵循“地理优先”,简单点说,医院获取的自愿捐献器官,优先用于自己医院的手术。
朱同玉认为,制度还不完善,“漏洞还在,一个医院有自己的OPO,会希望把器官资源留在本院”。
张雷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早期阶段,一个系统的可行性、合理性和合法性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逐渐去发展。“全上海设立一个OPO是最终的理想,我们当然希望国家建立一个大的器官资源库,这最理想,但不现实,现在只能依托现有的移植医院,以点带面,慢慢做起来。”
夏强也认为,上海建立一个OPO专职中心目前来看并不现实,他提出了一个技术上的考虑。“现在每家医院都在开展自己的手术,我们在系统上看到匹配的器官,不是本院的基本不敢用,因为器官不是商品可以随便流通,与很多技术因素有关,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有行业的特殊性。”
不过,夏强认为OPO系统还应该更灵活,需要完善。分配的公开、公平、公正是器官资源捐献的基础,但计算机是死的,人是活的,“比如一个病人我们前一天联系他时情况很好,今天匹配到他,但却找不到他人,或者他今天的条件不适合做手术,怎么办?这样情况下二次分配怎么开展?”夏强强调,“系统分配是一切的基础,不能允许人为操作,但这个系统还有很大完善空间,要做手术的一刹那,会有很多变数,怎么在优先的时间内重新分配,对我们来说是新的问题”。
“当然,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夏强补充说。
OPO活力有待激活
张雷认为,到目前为止我国探索器官捐献的这条道路是成功的,毕竟,三年前我们还很难想象会有现在一年一千多例的捐献量。“这三年来的发展状况,我认为是好于预期的。关键是现在我们开始重视这项工作,激发OPO的积极性。”
张雷直言不讳地表示,现在的OPO活力不够。“器官捐献工作能不能做得好,最终都是落实在一个个具体案例上的,OPO有没有这样的工作热情和效率,直接决定了效果。按照百万人口捐献率算,上海从2013年的百万分之0.25提高到去年的百分之2.5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如果达到百万分之10,在华人地区已经很好了,浙江等地已经达到,这说明上海的OPO活力还没有完全被激发出来。”
仁济医院副院长闻大翔对此亦有体会,在上海截至目前的79例自愿捐献中,52例来自仁济医院OPO,仁济的经验是,医院高层的重视与建立一支专业、敬业的团队。
仁济医院在上海的8个OPO里启动最早,组建了一支由副院长、医务处长担任主要负责人,与移植相关的各部门骨干构成的OPO团队。他们的经验表明,开展OPO工作的重点首先在积极主动地挖掘潜在的捐献者,仁济医院目前有6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在上海各家医院中算比较多的,而在一些OPO工作开展较好的省份,仅一个OPO办公室的协调员数量就多达十多人。
上海市卫计委划定给仁济医院的动员区域是浦东、长宁与嘉定三个区,对辖区内的13家设有重症医学学科的医院,仁济医院的OPO团队组织了近百场关于器官捐献和分配工作的宣教。“之前一些医护人员都不了解OPO,何况社会上的普通民众。”闻大翔认为提高医院ICU、神经内外科等部门医务工作者对OPO的认知率非常关键,一旦他们头脑中有了意识,对器官捐献事业取得认同,遇到潜在的捐献者就会主动联络OPO协调员。
记者采访了仁济医院的OPO协调员陈小松,他说,他的工作状态是24小时待命,经常只要接到有潜在捐献者的电话,哪怕是深更半夜,他也要立即赶到现场,因为从判定死亡到获取脏器的时间窗非常短暂,捐献时机稍纵即逝,稍微拖延时间就会失去延续生命的希望。
虽然目前仁济医院每十例潜在捐献者中大概才能成就一例捐献,但陈小松坚信只要社会对器官捐献的认知程度提高了,器官捐献成功数量就一定会上升。
如何实现器官自愿捐献
1 器官捐献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本条件?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并无绝对年龄限制,主要视捐献器官及组织的可用性而定。原则上,有关器官或组织的功能良好,没有感染艾滋病或者其他严重传染病,没有癌症(除原发性脑肿瘤)者,一般都适合器官捐献。
2 如果一个人想捐献他应该怎样做?
有捐献意愿的公民,生前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向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捐献办)或红十字会的捐献登记站申请人体器官捐献登记,办理相关的捐献手续。也可以在医院的宣传栏内获取资料,按照资料要求,自愿登记后有兼职协调员转交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也可以在红十字会网站填写报名资料。
3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有哪些方式:
1)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通过书面自愿申请人体器官捐献登记,并且没有撤销登记的,待其身故后进行的人体器官捐献。
2 )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器官,待其身故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达成一致意见,共同或委托代表以书面形式表达同意的人体器官捐献。
4 器官捐献的过程是什么?
医院兼职协调员在医疗机构中发现潜在捐献者,如果潜在捐献者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有捐献意愿,则由专、兼职协调员共同帮助完成器官捐献登记手续,公证相关资料,经院内会诊病情不可逆,并由医院组织联系(专职协调员协助)市级医学专家会诊评估组专家复核评估捐献者病情,如病情确不可逆,则经医院伦理委员会论证通过后报送捐献办,经捐献办确认已完成相应程序,将捐献者相关资料录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管理系统。
当完成登记的捐献者在临床上达到待捐献状态时,由捐献办通知获取小组,在救治医院两名以上医生确认并宣布捐献者死亡后,获取小组进行人体器官获取,获取小组根据人体器官捐献标准进行判断,确保有效捐赠,最后按人体器官获取标准进行器官切取并保存。
5 捐献完成后遗体如何处理?
器官捐献者完成捐献后的遗体,由医院进行符合伦理原则的医学处理,恢复遗体原貌,对于有遗体捐献意愿的捐献者,由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联系遗体接受站接受,对于没有遗体捐献意愿的捐献者或不符合接受条件的捐献者,由就诊医院移交其家属,会同捐献办协同处理善后事宜。
打破不均衡
记者采访仁济医院、长征医院与中山医院的明显感受是,专家们普遍反映OPO体系目前没有充分考虑到移植和捐献工作的地区不平衡性。目前,全国移植技术发达的医院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比如上海有11家医院可以开展移植。因为这个原因,上海各家医院里登记的等待移植患者,来自全国各地,数量很大。
缺移植技术的地方不缺器官,上海、北京等地区病人来自全国各地,但分配的OPO区域仅限于当地,病人多器官少,这样的现状,更需要国家层面对OPO区域划分的协调。
“我们中山医院只划定了上海徐汇、青浦、金山三个区,也就300万人口的覆盖面,而我们的患者却来自全国。”朱同玉说。他认为,器官分配系统应该考虑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的现实需求,为这些城市提供更多的器官资源。
张雷认为,目前的情况需要迅速做出调整,现在已经有医生因为没有手术可以做,换科室不当移植医生了,这是一种技术资源的浪费,牺牲的是患者的利益。
针对这种情况,夏强建议建立让自愿捐献动员工作做得好的OPO带动其他OPO,尽快将没有动员起来的片区开发起来,现在动作太慢,时不我待。
“在全国成立全国区域的OPO联盟,比如华东地区联盟,联盟内部可以协调技术与器官资源。我们得到器官,他们得到技术。”夏强认为如此可打破技术与器官资源两者不均衡的壁垒。脑死亡立法
闻大翔认为,OPO的第二个工作关键点在于死亡的判定标准。仁济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陈小松的体会是,在动员时,家属首先考虑的就是死亡判定问题。对于脑死亡标准,陈小松认为需要立法,目前中国以心死亡为主要的判断标准,家属对脑死亡标准抵触情绪很大,需要解释很久。
“器官捐献要随着全社会对死亡认知水平的提高才能做好,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此我呼吁对死亡问题,从中小学开始,教科书就要涉及。”陈小松说。
尽管目前面临各种困难,但陈小松依然很有信心,他认为只要有人去努力做这项工作,就一定会有成效。
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汤兆祥也强调了死亡法重要性。“让捐献工作有一个法律的依托,比如捐献者遗体归属权是谁。”当然,要实现捐献,有很多客观的制约,除了观念,还有病情、器官的质量等等。
现实操作中,如果一个人自己登记捐献器官,但直系亲属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捐献。张雷介绍,在上海,他们发现小孩子捐献的比较多,因为他们的父母比较年轻,接受了器官捐献的观念,家族里的阻力相对较小,容易做出捐献的决定。
“家庭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是当地人,社会关系很紧密,会有很多人插手这件事,发表意见。假如社会上有70%的人同意器官捐献,这已经是很高的比例了。
张雷前不久就遇到了一个放弃捐献的案例,一名因颅内出血转院至上海的患者,弟弟是当地红十字会的成员,原本同意捐献器官,但最终迫于家族压力,放弃捐献,“这实在可惜,如果捐献成功,至少可以挽救三个人的生命”。
张雷认为,器官捐献最重要的还是法制环境,对死亡界定不清晰,关于捐献意愿的表达也是模糊的。关于捐献意愿,国际上有几种方式,一个是事前登记,一个是默认,只要不说肯定不捐,就默认为捐。他认为法律一定要把相关问题界定好,划好红线,给从事器官捐献工作的人以保护,对捐献家庭提供保护。
让捐献变得更加温暖
现在,器官自愿捐献在现实中还遇到很多特殊的困境。朱同玉医生遇到过一名来自四川志愿者,他一直想无偿捐献自己肾脏,找了朱同玉很多次,但因为与政策违背未能如愿。按照规定,活体器官捐献仅限于亲属之间,只有尸体捐献才可以提供给陌生人,而这位四川志愿者显然不符合这两个条件。
张雷医生最近也遇到了类似的案例,一名男子找到他,想把自己的肾脏捐献给战友的儿子,战友十多年前牺牲后,子女就一直由他照顾,感情犹如亲生子女。“我只能建议他去民政局办理寄养手续,尽管他们的关系事实上是收养关系,但现在去补办手续,也很可能无法通过审批。”
中国对捐献者的身份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主要是担心存在交易。张雷认为方向是对的,但不能一刀切,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汤兆祥介绍,为了鼓励自愿捐献,目前对捐献者的家庭,红十字会从人道主义出发给予一系列的关怀措施,首先,在精神层面,征得家属同意后,红十字会会在社会层面宣传和赞扬捐献者的事迹,上海在福寿园建有器官捐献者的纪念碑,“如果亲属同意,我们会把名字刻在纪念碑上,对他们有纪念活动,福寿园的电子触摸屏上,有捐献者的音容笑貌,可以在整个园区播放。”
对于因捐献者逝世而给家庭带来经济压力的家属,红会会减免合理范围的医药费用,善后费用也可以核报,并解决近亲属在捐献期间的食宿。另外,亲属可以向红会申请人道救助。
汤兆祥强调,人道救助是在自愿捐献的前提下进行的,不是交易,更不是买卖,目的是要把这种大爱精神传承下去。
陈小松呼吁不能功利地去看待救助捐献者家庭,他提议 “全社会要共同努力,让捐献变得更加温暖。”
器官自愿捐献与移植系统之于中国,就像一个移植器官之于新的身体,在中国运转还要经历“排异”关。
【文献来源】https://www.zhangqiaokeyan.com/academic-journal-cn_xinmin-weekly_thesis/02012474388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