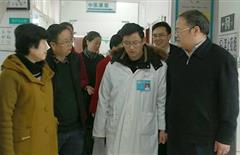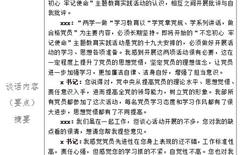驴的故事(二)
发布时间:
驴的故事(二)
灾难
那是一头特别健壮的大骟驴,胖嘟嘟的,毛色灰黑,唯有眼圈周围和四只蹄子上长着细细的白毛,我们不惜把夸赞骏马时才用的“四蹄踏雪”送给了它。它呢,甚至比一匹骏马还有用,驮水打场犁地磨面,样样农活都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它很乖巧,妇女娃娃们使唤它,从来不发脾气,不像有些人家的驴子,你说东,它偏西,所谓“驴脾气”;或者,稍不顺心就摇头摆尾地尥蹶子,这是“犟驴”。我们家的骟驴却十分温顺,甚至有点逆来顺受的味道,比如,驮水的时候,我常常从它屁股后面爬上去,它既要驮水又要驮我,也丝毫没有不高兴的意思。
就是这样一头堪称模范的驴子,正值盛年的时候,却遭受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有一天,我驮水回来的时候,照样是骑在驴背上的,若在平时,大人们见怪不怪,也就不说什么了,可是那一天,奶奶却突然说:“你这个小先人,没有长腿吗,你看,驴的腿都瘸了!”我赶紧从驴屁股上溜下来,看到大骟驴真的一瘸一拐的,似乎是左前腿受了伤。我有点害臊,虽然不是我把它弄瘸了,可是骑在一个驮了两桶水的瘸驴背上,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幸亏是奶奶看见了,如果是父亲,说不定会踢我两脚。我嗫嚅着说:“不知道,昨天还好好
的......”奶奶和小叔把驴背上的驮桶卸下来,让小叔看看骟驴的左腿究竟怎么了。小叔和我很仔细地查看,还用手上下摩挲,与右腿反复比较,没有发现外伤、肿块和其他异常情况。小叔又让我拉着骟驴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可能是卸了驮桶的缘故,虽然还稍微有点跛,但比刚才好多了。小叔最后的结论是:“问题不大,可能在石头上磕了一下,缓一缓就好了!”我松了口气,赶紧去窑洞里背来一筐草,比平时格外多些,似乎有赔罪的意思。
此后连续几天,我仍旧赶着大骟驴去驮水,只不过再也不敢骑了。我发现,大骟驴腿瘸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善,而且有加重的趋势。我跟在大骟驴后面,看着它背上驮着沉甸甸的水桶,身子一下一下往前倾,头一点一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在往驮桶里灌水的时候,没有像平时那样灌得满满的,而是留了点空隙,算是对大骟驴的一点帮助吧。回来后我主动报告奶奶,说大骟驴瘸得更厉害了。奶奶皱了皱眉头,说:“和你小叔叔拉到铁匠那里去看看,是不是蹄弯里卡上石头了!”庄子上有个铁匠,经常给套马车的辕马和拉稍子的牲口钉铁掌,对牲口蹄子上的毛病有点办法。我和小叔拉着大骟驴去找铁匠,他正在铁匠铺子里忙碌,看也不看就说:“驮水的时候多骑一下就好了!”这话明显是冲着我来的,灰条岭所有的人都知道,驮水的时候骑在驴背上的只有我一个。我有点恨这个铁匠,觉得他太多嘴,同时也隐隐担心,似乎骟驴的腿瘸与我有直接关系。小叔倒很随和:“老哥,你看看吧,是不是蹄子上有毛病?”铁匠磨磨蹭蹭地套上一个又脏又破的帆布围裙,拿一个一尺多高的小板凳放到大骟驴跟前,他轻轻用手磕了一下驴的膝盖,大骟驴听话地把瘸腿弯起来,蹄子放到小板凳上让铁匠看。铁匠拿一个小錾子在驴蹄子里挖,突然,大骟驴象触电一样跳起来,差点把铁匠踢翻。就是这一跳,让铁匠找着毛病了,他肯定地说:“踩上钉子了!”我和小叔都有点纳闷,央求铁匠想想办法,铁匠让小叔抱住
驴头不松手,又是一阵折腾,大骟驴浑身颤抖,铁匠满头大汗,费了很大的劲,终于从大骟驴的掌心里拔出一根一寸多长的铁钉。我攥着那根铁钉,左思右想弄不明白,它是怎么钉到驴蹄子里的?铁匠说:“扎得太深,伤着骨头了,说不定把这头驴废了!”
我和小叔忧心忡忡地拉着骟驴回家。心里想,自己真是太顽皮了,驮了水还要骑上它,太不应该。又想,好驴有好报,说不定它会慢慢好起来的。那时候,如果采取一些消炎的措施,或者让它歇缓几天,也许会好一些;但条件有限,再说我们家只有一头驴,驮水的事非它莫属,尽管一瘸一拐的,每天一次的驮水从不间断。期间,家里人商量过,要不要买一头驴来替换大骟驴,但由于手头紧张,都没有落实。这样一头几乎残疾的驴,卖吧,没人要;不卖吧,白吃草料不可能,就勉强驮水吧,什么时候实在不行了再做打算。
就这样,我每天赶着瘸腿的骟驴去驮水,再也不敢爬到驴背上了。庄子上驴的队伍里,它被看作另类,驮水的时候走在最后面,吃草的时候,只要看到别的驴过来,它就默默地避让。春天,别的驴都四蹄生风互相追逐,只有它,站在一旁黯然伤神。更让人揪心的是,它一日一日地瘦下去,毛片灰暗破败,耳朵耷拉着,眼睛无精打采,有几次,我看到它的大眼睛里蒙着一层薄薄的泪光。整整两年,大骟驴风雨无阻,仍旧用瘦弱的身躯一瘸一拐地为我们家驮水。我能做的,就是尽量不把驮桶灌满,稍微减轻一下它的负担。它受伤的蹄子,变得格外丑陋,坚硬的角质层夸张地延长了一大截,像套了一只破鞋。有一天路过铁匠铺子,老铁匠一反常态:“过来过来,我看一下它的蹄子。”他把大骟驴畸形的长蹄子放到小板凳上,拿一把锋利的铁铲,“吭哧吭哧”地铲了好半天,把多余的角质层铲掉,同时还用凿子挖出许多锯末渣一样的东西。我好奇地问老铁匠那是什么,老铁匠故作神秘地说:“瘘!”后来我才知道,农村里,把牲口蹄子受伤、感染流脓又结痂的过程叫“生瘘”。自从那天老铁匠“挖瘘”以后,大骟驴的情况逐渐好转,虽然还有点瘸,但比以前好多了。
又是半年,大骟驴的腿基本恢复了,但经此一难,它明显地衰老了,瘦骨嶙峋,眼里弥漫着一片哀伤。虚惊
我们家还养过一头驴,一头小叫驴,是个“软腰子”,不管给它往背上驮什么,哪怕是用手轻轻捋一下,它的腰总是会弯一下,然后慢慢直起来。奶奶说,可能是小时候脊梁被什么撞击过,受了惊吓,以后就习惯性地有了弯腰的动作。虽说是“软腰子”,但不影响干活,只要腰子直起来,就与别的驴没有什么区别了。
有一年,山里雨水特别多,不是暴雨,也不是连绵的阴雨,而是静悄悄软绵绵的那种雨,多半是天黑下、天明放晴,三五天就是一场。那时候还是生产队,生产队的豌豆种在丁家大槽里,离我们家很近。队长安排杨老汉看管豆地,用农村里的话说,杨老汉是个“铁眼珠子”,任何人别想摘一颗豆角。我们虽得地理之便,却无摘豆角之实,暗地里都咒骂杨老汉。看着那些红的白的豌豆花开了一层又一层,看着那些青翠鲜嫩的豆角一串一串地缀在豆秧上,我们心里
痒痒的,做梦都想吃豆角。我们家和杨老汉家在一个院子里,平时杨老汉都在豆地周围巡逻,偶尔来家里一趟,我们便赶紧跑出庄门,想乘机摘几个豆角。可是我们前脚出门,杨老汉端着饭碗后脚就跟出来,我们故作镇静地在田埂上抓蝴蝶,偷眼瞅杨老汉,见他一双鹰眼盯着我们,只好悻悻返回。就因为这个缘故,才引发出后来“软腰子”丢失的事。
上学的时候,邻近生产队的娃娃们口袋里装着豆角,那种特殊的清香让我直流口水。打听得知,他们的豆地在韭菜沟里,从我们家出发,朝北翻过一座山梁就到了。我打定主意,要去偷一次豆角;并且想好了,摘来的豆角要当着杨老汉的面“咔嚓咔嚓”地吃。我做了一些策划,吃过晚饭后,牵着“软腰子”出门,说是去放驴,天黑才回来,如此三四天,大人们都不怀疑了,倒是小妹神秘地朝我吐舌头。一个天边有几缕晚霞的黄昏,我把书本藏在驴槽里,把空书包掖在衣服底下,牵着“软腰子”出了门。心“扑通扑通”直跳,满脑子都是豆角啊!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让“软腰子”这里吃几口那里吃几口,天黑前就摸到韭菜沟里的豆地旁边了。真是一块很大的豆地!远远就能闻见了豆角和草木混合的清纯气息,湿漉漉甜丝丝的,让人直想打喷嚏。我把“软腰子”拴在离豆地有一段距离的路边的芨芨墩上,蹑手蹑脚进了豆地。刚开始还是有点害怕的,爬在豆秧子底下不敢出声,四下里一片寂静,西边天空中挂着金色的月牙儿,象铁匠铺子里烧得通红的镰刀。豆角长得太繁密了,一抓就是一大把,毫不费力就把书包填满了。我从地上坐起来,一面吃,一面把两个裤兜兜也装满,打算回去给小妹。这时,不远处似乎有说话的声音,我赶紧趴下,屏住呼吸观察动静,风哗啦哗啦地吹过,渐渐没了声息。
摘豆角的过程很顺利,我背着鼓胀的书包打算骑着“软腰子”得胜回家,到拴驴的地方,才发现驴不见了!我的脑袋“嗡”一下,心跳又加快了,比刚才偷豆角时更为剧烈!拴的好好的,不可能挣断缰绳跑掉吧?就是挣断缰绳,也应该在附近的麦子地里吃粮食,不会跑到别处去。夜色并不太浓,似乎有一丝雾气,模糊的月光下,一头驴子的轮廓应该能看得清楚,可是我找遍了周围的沟沟岔岔坡坡梁梁,就是不见它的踪影!驴是山里人的命根子,没有了驴,用什么驮水?没有水,怎么生活?我一屁股坐在地埂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点后悔自己单打独斗的冒失行为。可是,一切都晚了,驴不见了!都怪我摘豆角心切,一时疏忽,没有把驴拴在隐蔽的地方而是拴在了路边,走夜路的人顺手牵驴,正好骑着它好赶路!
我大概是吓傻了,不敢回家,又不知该怎么办,想哭又哭不出来,咧咧嘴,只发出低低的嘿嘿声。我感到自己把死的罪都犯下了。月牙儿隐去,夜气开始变浓,冰凉的湿气从脚底下往上升,我小小的身子有点颤抖。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边的山梁上,传来一个弱弱的声音:“双喜——双喜——”声音似乎被夜色黏住,传不多远,但我听清楚了,是奶奶在叫我,我的眼泪哗啦流下来,从地上站起来,腿有点发麻,却不敢应声。“哥,在哪里?”是小妹脆生生的声音,同时又听到“咔!咔!”的干咳声,父亲也出来找我了。我“哇”地一声哭出来,心里反倒不是很害怕了,反正驴已经丢了,一顿打是免不了的,剩下的事,就靠大人们处理了。我抽抽噎噎地述说了“软腰子”丢失的过程,强调我主要是出来放驴,顺便摘了几个豆角。奶奶踮着小脚走过来,
压低声音说:“快跑,你爹拿着鞭子!”我转身跌倒爬起地朝相反的方向跑,
后面父亲的鞭子“啪——”地甩响,仿佛一声炸雷,把静谧的夜划开一道口子。听小妹说,那天晚上,父亲安排奶奶和小妹返回,意思是把我也叫回家;他带着二姐又在周围找了一遍,当然比我走得更远一些,还是没有找到“软腰子”。后来父亲说:“现在黑天半夜的,上哪里找?明天发动生产队上的小伙子,走南营上凉州,实在找不着,就可能被人煮到锅里了。”
父亲他们心事重重地回来的时候,正好碰上小叔叔从生产队开会回来,奇怪的是,小叔叔的手里竟然拉着我们家的“软腰子”。原来,民兵连长召集附近几个庄子上的民兵开会,我摘豆角的时候,开会的民兵路过拴驴的地方,见周围没有人,出于好意,把驴拉到生产队的院子里了。同时去开会的小叔叔,散会后就把驴拉回来了。
驴是“找”到了,尽管虚惊一场,但家里人还是要对我进行教育,大家吃着豆角,七嘴八舌地指责我不该单独行动。后来奶奶摸着我的头说,娃娃们连个豆角也吃不上!隐约表达了对杨老汉的不满,也算是对我过失的原谅。
驴的故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