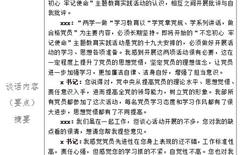知青岁月:《大众电影》的故事
发布时间:2011-03-09 09:40:21
发布时间:2011-03-09 09:40:21
《大众电影》的故事
郑启五
《大众电影》是新中国期刊中的“老字号”,在几代影迷心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我心亦然。
1969年我从厦门来到闽西的山沟里插队落户,曾有一次摸黑步行十几里小路赶到公社看一场“准黑白电影”——《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称之为“准”,是因为那片种为“屏幕复制片”,本专供电视台播映的,但“为了满足工农兵和革命群众的要求,特在全国城乡隆重献映”。如此便是我插队初年看过的唯一影片!既便是春节返城探亲,影院遭遇的只有“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剧中台词,影迷们早已烂熟,片中人说了上句,满场面无聊赖的影迷们便异口同声地嚷出下句。那时的文化娱乐生活,一如置身荒漠。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我喜出望外从邻队知青吕晓声的破麻袋里掏出了二大册的《大众电影》合订本!这不啻是荒漠甘泉!我如饥似渴,早晚一有空闲就埋头于那黄皱软烂的书页的发出旧纸特有的气味中。吕友告之,这几册“宝书”是红卫兵查抄图书馆时,他“火中取栗”,东掖西藏一路有惊无险带到”广阔天地”来的。
旧《大众电影》的画页与文字—一复活了我脑海中多年积存的老电影。深夜爬上我垫着稻草的床,漆黑的夜里便飘忽起一方银幕:《冰山上的来客》“阿米尔,冲!”《斯大林格勒大战》战车隆隆,卡秋莎呼天抢地的怒射;《五朵金花》、《阿诗玛》、《芦签恋歌》……竟交替而来。当然只有我能看到听到,偶尔兴起,我会跟着哼哼“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尤其令我激动不已的是在一本20世纪50年代的《大众电影》上,凭生第一次拜读施蛰存先生的大作,内容是评点法国故事片《第六纵队》的。施先生才华横溢,早在30年代便是风靡大上海的小说家,与鲁迅先生有过文字纠葛,被鲁迅怒斥为“洋场恶少”。1940年应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标之聘,施教授千里辗转,来到因躲避日寇炮火而内迁闽西山区的厦大执教,由此与一批酷爱文学的奉辛学子结下“战乱之谊”,其中便有我的父母亲。(令尊大人对“恶少”评价极高,平易近人是绝对的,不知当年鲁迅是否骂得过火。)想来这真是人间奇缘:我们一家两代人在两个迥然各异的动乱年代,却因流落到同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边贫山区,与同一位国学大师结下此生缘份,时至今日,我家与年近百岁的施先生仍有书信往来!
文革结束后,老电影被冠之“复映片”竞相挣脱枷锁重见天日。中国电影放映史上迎来了最辉煌的岁月:观众日日如潮,电影片片“火爆”。厦大海岸线上陆军与海军的电影放映队你去我来,爽人的露天电影带给我无数个丰美的夜晚。我凭着当年在闽西山区熟读三大册《大众电影》的造化,孜孜不倦地写起了电影评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数以百计的长文短论,散发在大江南北的影刊影报上,并由此在市影评界落得几个诸如“副会长”、“常务理事”的虚衔。
然而我迟迟不敢向《大众电影》投稿,她是我心中顶礼膜拜的圣殿——敬重的施先生说话的地方。我唯有一期期地拜读,一本本地珍存。直到20世纪90年代,《大众电影》开辟“影迷天地”,我才鼓足勇气,给她投寄了一篇多情的散文——《怀念露天电影》,刊发在1991年第10期上,
文章刊出时,那种幸福的感觉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199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