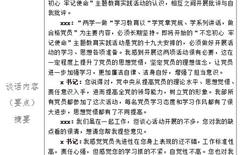张爱玲小说
发布时间:2012-12-02 19:21:27
发布时间:2012-12-02 19:21:27
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命运
摘要:对于女性的命运,多年来总有人在研究,但总不得全面,复杂的世界带动了丰富的人生,却也造就了许多悲苦。在张爱玲的笔下,总是有很多说不尽的苍凉,道不尽的心酸。无论是哪一种的两性关系,女子的地位总是卑微的;因为心欲,因为生存,女性总是难免悲哀。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 爱情 命运 软弱
张爱玲(1920——1995)笔名梁京,出生于一个曾经显赫的阀阅门第,她家既有前朝的繁华,又较早的接受了西方文化,其父张廷众是一个典型的封建遗少,而母亲董逸楚则是一位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女性,父母因性情不合终止离异,父又续娶,正是这种家庭环境造成了张爱玲忧郁、冷漠而又极度敏感的性格,终于在一次被父亲毒打、囚禁后逃离了父亲的家,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因为生活苦闷,张爱玲读书很用功,同时幻想以写作成名。[1]1943年——1945年是她创作的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她陆续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小说,同时也发表了多篇散文,在当时可谓盛极一时。在张爱玲的笔头下,表现出的是女性的悲哀,人的劣根性及道德的残缺。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张爱玲真正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女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受的内外压力:有来自旧家族内部的冷漠,有来自命运的捉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现在我们将带着她的作品来分析其中独特的女性人物的命运。
《金锁记》是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中的重要小说,而曹七巧则是《金锁记》中刻画最深入细致的一个的主要人物。张爱玲曾在其小说集《传奇》的开头写道:“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而《金锁记》中曹七巧这一人物正是对这句话的具体而生动的诠释。曹七巧的一生是20世纪初无数出生低贱最后变为贵族妇女的众多妇女的综合,她是从无数个20世纪初经历起起伏的妇女的经历中幻化出的一个人物。她是平凡的,平凡在于她的悲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里俯首可拾;但她又是不平凡的,因为,在她身上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意义。
《金锁记》以一个日趋衰败的世家望族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小家碧玉的大姑娘曹七巧,在世俗与命运的安排下阴差阳错地嫁入姜家豪门大院。而在畸形的婚姻和封建大家庭的无情戕害中她逐渐丧失人性,取而代之的是金钱欲的极度膨胀,最后成为一个丧失了人性的“疯子”的母亲形象。
七巧作为一个女性,长期的爱情生活得不到满足,性本能受到强烈的压抑,再加上出身卑微,在门第森严的大家庭里人格受到排挤和歧视,于是造成她的心理变态,沦为“疯子”。她要发泄、要报复,自己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别人毁坏了她的一生,她也要毁坏别人的一生。于是,她的两个儿女成为她破坏下的牺牲品。更为可怕的是长期的性压抑,造成七巧潜意识中的乱伦意念,“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一个男人”,“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她这一个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他也保留不住——他取了亲。”七巧这样想着,就“把一支脚搁在他肩膀上,不住地轻轻地踢他的脖子。”七巧在潜意识中是把儿子当作一个真正的男人看待的,是变相的占有自己的儿子。爱而得不到,这对七巧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在她对爱彻底绝望后,她那难以抑制的情爱欲转而成为对儿子的占有欲,对媳妇的摧残欲,对女儿的控制欲。
张爱玲对《金锁记》描绘的那个年代已离我们远去,可主人公曹七巧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思索。七巧给自己套上了金钱的枷锁,她的爱情是畸形的,人性也在不正常的生活环境下泯灭,但她的形象是那个社会的典型与真实写照,她的悲剧产生于金钱的枷锁,但根源在于封建家庭和吃人的旧中国。
《半生缘》是张爱玲的旧作,原名《十八春》,又名《惘然记》,1951年张爱玲以梁京这一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后来在其旅美期间进行修改,删掉了略带政治色彩的结尾,易名为《半生缘》,这是张爱玲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
《半生缘》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地点是在温婉、凄迷的旧上海。作者以第三人称开头介绍:“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来已经有十四年了”,然后写道:“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的工夫,这几年里面却经过这么许多事情,彷佛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乐都经历到。
顾曼桢、许叔惠、沈世均三人同在一个工厂工作,曼桢个性温柔坚强,叔惠开朗活泼,在相处中,曼桢与温和敦厚的世钧相爱了。曼桢的姐姐曼璐为全家的生计着想,十七岁时毅然离开初恋情人张豫瑾开始了舞女生涯,但家人并不能真正理解曼璐,认为她丢尽了家人颜面。如今曼璐年华老去,为了后半生有所依靠,决定嫁一个靠得住的人,这个人就是祝鸿才。从此,维护"祝太太"这个名分成了她最重要的生活支柱。
世钧与曼桢的爱情也受到了来自家庭的压力,加上两人的互相猜疑,后又有姐姐、姐夫的算计、陷害,他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是曲曲折折,不那么顺利。
婚后,祝鸿才发了不义之财,原形毕露,在外花天酒地。曼璐为保住自己的名分,决定生一个孩子来拴住祝鸿才,然而自己以往的几次堕胎使她有心无力。她一心想要拢络丈夫,知道丈夫有意染指二妹,不惜装病设计,让丈夫强奸得逞,将妹妹幽禁一年,生下一个男孩。唯恐沈世钧来找曼桢,还将母亲全家迁往苏州,沈世钧找到她时,她假说妹妹妹已嫁人,并且代妹妹退还他订婚戒指。后来,生产后,曼桢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逃离医院,找到教书的工作,不幸又被她母亲找到,劝她和鸿才结婚。曼璐也抱来她的儿子相求,她仍不为所动。后来遇见曼璐的女佣阿宝,知道曼璐病死,祝鸿才经商失败,就住在附近。出于母性,她常常留意年龄相近的小孩。后来,儿子得了猩红热,祝鸿才又常常不回家,她为了救小孩,留在祝家中照顾小孩。最终,为了孩子。她抱着自杀的心理嫁给了她平生最恨的男人——祝鸿才。婚后祝鸿才发了国难财,又花天酒地,曼桢决心离婚,独力工作;扶养孩子。
沈世钧婚后也搬到上海,始终难以忘记曼桢。由于共同的朋友许叔惠,二人得以再次见面。沈世钧说曾去找她,她姐姐告诉他曼桢嫁已给张豫瑾。曼桢告诉了他中间发生的曲曲折折,他没有想到她姐姐竟做出这样的事来!两人见面,对望半晌,曼桢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
没有爱的人偏偏结合在一起,而相爱的人却又咫尺天涯。在这场爱与恨的纠葛中,顾曼桢毫无疑问的成了我们为之愤慨的对象。 《半生缘》中顾曼桢是新女性,有知识,温柔而坚强,对家人有责任心,对姐姐的经历同情理解,但是,这个善良、勤恳、与人为善的好人,最后除了抢回自己的亲生儿子以外,一无所获。她不但没有得到上天的眷顾,反而遭到天“谴”:被姐姐算计、被姐夫强暴、被姐姐姐夫联手幽禁以至怀孕生子……这些近乎荒唐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离奇的发生在曼桢的身上,可以说,她的悲剧是由她周围的一个个的女人所造成的。先是母亲无意识的错误所导致的悲剧,之后又是姐姐有意识的错误所导致的悲剧,再加上沈母烧毁求救信的事件,使得这一个女人的一生充满着悲哀。
张爱玲笔下的顾曼桢,其坚强或者对命运的忧郁都是来自骨子里的。她是三十年代大上海的新女性,她坚强而自信,知性而素雅,她象夕阳的余辉一样,散发着一种沧桑美。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她都要求独立。曼桢性格中最大的特点除了坚强还有坚贞,即使是丢了一只旧手套,她也觉得很可惜,更何况是自己深爱过的人呢?而且一旦失去了,曼桢对新的物新的人就再也不会有从前这般兴趣了,这或许也就是曼桢离开世钧之后再也没有幸福过的原因。虽然后来她还是照样活下去了,但她仿佛整个人陷进泥潭里去了,神情恍惚。
顾曼璐,这个一生都“逃不出宿命的掌心的”不幸的女子,作为一个女人,她有着一个舞女被后辈抢饭碗的哀怨,一个年华渐逝的女人拼命想抓住一点东西的急切。可是一切都没有朝着她意愿中的方向发展,她一辈子惟一爱过的男人是张豫谨,但为了全家老小,她舍弃了她心中所珍视爱情,把它深埋心底。祝鸿才是她的救命稻草,但她却为他延续香火,她最后什么都抓不住了。当张豫谨移情曼桢,曼璐从18岁时为家庭承担的苦楚释放了,她利用了自己的妹妹,为祝鸿才生了一个儿子。她的一生虽短暂但却充满了坎坷,由于生活的压力,逼迫着这个女子由妥协走向精神变态的深渊。
由对张爱玲《半生缘》中顾氏两姐妹的形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作为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的存在的艰难,无论是社会环境的影响,还是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积习,还是女性自身思想等的禁锢,女人要实现自我价值,把握自己的命运,都要经过不懈的努力,也需要长期的斗争。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小说中比较突出的一篇,小说连载于《上海杂志》月刊后,在当时赢得了读者群极大的回响。而其在一九四四年改编成话剧上演之后,更造成了万人空巷的盛况。《倾城之恋》不仅在当时使张爱玲的声誉达到高峰,并为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奠定了重要的地位。 《倾城之恋》这个题目乍听起来会以为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但读后才明白,所谓倾城是说一个城市沦陷背景下方可成全的一段婚姻。所以,从整体而言《倾城之恋》是描写普通人乱世中的“传奇”,从而寻求那份最后回归的普通。
张爱玲以一贯苍凉的叙述基调,特有的敏感笔触娓娓道来一段浮华背后的无奈与凄美,讲述了一个没落世家女性生存困境的悲剧故事。在长达三万多字的篇幅中,描述了女主角白流苏对于婚姻的赌注。而故事的内容则可以以1944年4月7日署名迅雨的论述作为概括:一个破落户家的离婚女儿,被穷酸兄嫂冷嘲热讽撵出母家,跟一个饱经世故、狡猾精刮的老留学生谈恋爱。正要陷入泥沼里时,一件突然震动世界的变故把她救了出来,得到一个平凡的归宿。
《倾城之恋》开篇第一段,就让人感觉到浓重的腐旧气息。白公馆里,“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在上海这个中国近代现代化最早的城市里,生活的步骤是快的,别人的时钟都拔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仅一句话,就点明了白公馆是这个近代大都市里的守旧部落。 生活在这样一个压抑的、畸形的旧式家庭中,对流苏来说,唯一的出路、最后的选择是离开。流苏大抵上是一个坚强的女子,她会反抗,能够大胆地顶着众人的唾弃与前夫离婚,可见是很有勇气的。然而流苏也是妥协的,因为最终她也不过是一个在经济上柔弱、无助的女子,逃离的方式只能是依靠男人来寻找自己的栖息之地。她不得不学会算计,不幸的生活告诉她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自己,才能生存下去。 徐太太的适时出现在文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先是开导流苏后又说为流苏留心着,正是由于徐太太的牵引,让流苏有了反击的希望,让她对自己有了一点信心,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流苏回到屋里,端详着自己: 还好,她还不怎么老。她那一类的娇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永远是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 她的脸,从前是白得像瓷,现在由瓷变为玉——半透明的轻青的玉。下颌起初是圆的,近年来渐渐尖了,越显得那小小的脸,小得可爱。脸庞原是相当的窄,可是眉心很宽。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 文中的描述成功的勾勒出流苏娇美的形象,为下文做了铺垫,正是由于流苏典雅脱俗的美,具有中国女人的特征,所以在女人堆中打滚多年的柳原才会注意到她。而在与范柳原交往的过程中,流苏经历了一番内心的争斗,这场爱恋于她来说,更像是下的一场赌注——婚姻的赌注,这赌注的第一步便是随从徐太太远赴香港。范柳原是一个有钱的华侨和他在伦敦的交际花情妇生下的儿子,由于他父亲在中国有妻子,柳原充其量算一个庶出的,而当母亲去世后,孤身一人流浪伦敦“很吃了些苦”。父亲故世后,才获得继承权,却得不到整个家庭的尊重和认可,成了一个浪荡公子。这时流苏在他的视野里出现了,她的低头,适合穿旗袍,会跳舞,含蓄的美在相亲当天攫取了他全部的目光,流苏吸引范柳原的绝不仅仅是美貌,还有一种或许柳原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流苏抵港的第一天,两人在浅水湾饭店的对话,开始了两人之间的交往。柳原道:“有人善于说话,有的人善于笑,有的人善于管家,你是善于低头的。”流苏道:“我什么都不会,我是顶无用的人。” 柳原笑道:"无用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 而当柳原反问流苏自己是怎样自私时,流苏并没有把心中真正的想法说出来,反而是迂回的偏着头笑道:“你要我在旁人面前做一个好女人,在你面前做一个坏女人。”接着又解释道:“你要我对别人坏,独独对你好。”流苏叹了气道:“我不过是一个过了时的女人罢了。” 而听完柳原对萨黑夷妮的身世描述之后,流苏自卑自己只是个穷遗老的女儿,身分还不及她高。但柳原却道:“你放心,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拿你当什么样的人看待,准没错”。这里我们看到两人之间的互动,从字里行间里看出两人都在不断试探对方,文中有这么一段:从浅水湾饭店过去一截子路,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桥那边是山,桥这边是一堵灰砖砌成的墙壁,拦住了这边的山。柳原靠在墙上,流苏也就靠在墙上,一眼看上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她的脸,托在墙上,反衬着,也变了样 ——红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张脸。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流苏和柳原的互动有许多地方都是出于心计的,一个是传统的女人期待婚姻,一个是漂泊的浪子想找情妇,柳原对流苏是如此的迂回、曲折;流苏对柳原是如此的矜持、含蓄,香港之行是流苏人生的一次赌博,流苏进行着异常的心灵之旅,一场心智的较量。
流苏赌注的第二步就是返回上海。白流苏回到了上海,但是她知道范柳原对她没有绝望,她不愿服输,她不能就这样自贬身价,她是会应付人的,很懂得交往的技巧,她懂得以柔弱示人,以退为进,以弱胜强。在交往的过程中,感情应该是双方平等自愿的付出,感情是需要时间来磨合的。虽然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她的旧式家庭,但她对这个家庭是不报以怎样的希望的。她知道她还是会离开,这只是她停泊的中转站。她仍为得到一个平凡的归宿而盘算着:她和这家庭早是恩断义绝了。当范柳原寥寥数字的一封电报叫流苏重返香港时,面对白老太太那句“既然是叫你去,你就去罢!”再一次看到了这个家庭的冷漠和生活在这种腐败家庭中的悲哀。白流苏毅然选择再次赴港,为自己重新找到生存的依靠,因为来自家庭的压力,这也是流苏无奈的选择。
而第三步便是再次赴港。两人在细雨迷蒙的码头上相见,他们终于抛却了以往的矜持,有了第一次相吻。“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始终不肯冒失。现在这忽然成了真的,两人都糊涂了。”但是范柳原对白流苏的感情,还没有到让他放弃自由的地步,他可以给流苏物质上的保障,但不能给她婚姻的承诺。当恋爱不在纯粹,让人感到悲凉。
但最终,或许是一次战争成全了他们。流苏与柳原终于结婚了,但战争消解了太多的东西,她们彼此并不互相了解,爱得也并非真切与彻底,他们的婚姻不是因为惊心动魄、生死相随的爱情,而是因为战争的成全。在小说的最后,男女主人公有一句很经典的对话,流苏说:“你早就说过你爱我”。柳原笑道:“那不算,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乍读起来,有些莫名,细想来才发现有太多的韵味包含其间,既然不算恋爱算什么呢?在爱被还原到如此透彻之后,人自私的本质便完全呈现出来,让人感觉到爱情的苍白。
《倾城之恋》是一场爱情的战争,正是一段战争里成就的爱情,这对男女间曲曲折折、遮遮掩掩的爱情,张爱玲以明褒暗贬的手法,参差对照的写法,讽刺了现代社会中男女功利的爱情。“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这样的姻缘美满反倒暴露了人生不可靠这个更大的缺憾。 所谓惊天动地的爱情亦不过如此!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在封建社会背景下不同的女性形象,并选取不同的视角去揭示她们悲剧式的命运。生活在那样一个家族里面,张爱玲的性格也具有多重性,她既有母亲新潮的思想,能够将故事中的女性敢于反叛的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同时她也受到其父的影响,在封建势力的面前,女人的命运也总是逃不出宿命的安排。她可以让小说中的女性有个性,如白流苏,在那样一个女性地位低下的时代,毅然决然的选择了离婚这条道路,而她自己在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却如此的脆弱。
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有一个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的中年男人。当他看到一篇小说时,才刚读了个开头,就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他读的小说就是张爱玲的《封锁》。
胡兰成是浙江嵊县胡村人,生于1906年。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赤手空拳拼天下。他原有个发妻玉凤,在玉凤过世之时,胡兰成借贷以葬妻魂,却四处碰壁。对此,胡兰成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 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就是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身闯世界的文人,在挣扎中淡漠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观。所以在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拉拢人才时,他们看上了胡兰成。而胡兰成也不顾是非黑白地应允,成了民族的罪人。
此时的胡兰成,已在汪伪政府中任职,正在南京养病。当他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封锁》的时候,喜不自胜。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极愿与作者相识。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这更是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苏青,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但胡兰成执意想见,向苏青索要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胡兰成如获至宝。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胡兰成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她住的赫德路与他所在的大西路美丽园本来就隔得不远。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胡兰成却不死心,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第二天,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不久就到了。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又自己亲自去见他,主意变得好快。其实早前,胡兰成因开罪汪精卫而被关押,张爱玲曾经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说过情。因此,她是知道他的。于是,就这样见面了。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他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之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像个作家,倒像个未成熟的女学生。但他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失礼的,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人已有了知交之感,所以张爱玲倒未觉得胡兰成的话很唐突。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他忽然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句话,就忽地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这怎么可以”的潜台词是从两个人般配与否的角度去比较的,前提是已经把两人作为男女放在一起看待了。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真的是非常好。
次日,胡兰成去回访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他不安,胡兰成形容说,三国时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兵气。那天,张爱玲穿了一件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多年后,胡兰成对这些细节都有着清晰的回忆。此后,他每天都去看张爱玲。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但很快,他们恋爱了。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似乎是他们最初相识的延续。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他不回美丽园自己的家,而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先去看张爱玲。两人每天在一起,喁喁私语无尽时。但当时世人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只觉得胡兰成的政治身份是汉奸,又有妻室,年纪大到几乎可以做张爱玲的父亲。世人都觉得这样的爱情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都是为张爱玲惋惜的。她却不觉得。
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仅仅这一个“懂得”,也许就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其实细细分析来,张爱玲本身就不是一个世俗之人,她不以尘世的价值观去品评一个人。她没有什么政治观念,只是把胡兰成当作一个懂她的男人,而不是汪伪政府的汉奸;对于胡兰成的妻室,她也不在乎,因她似乎并不想到天长地久的事。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也许她只在乎胡兰成当下对她的爱,其他的,她都不愿多想。胡兰成的年龄比她大出很多,但这也许又成了她爱他的原因。
张爱玲从小缺乏父爱,便容易对大龄男性产生特别的感情,所以,年龄问题也不是障碍。于是,她倾尽自己的全部去爱他了,就这样在世人诧异的眼光中相爱了。爱得那样的超凡脱俗。
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这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结婚。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因为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自己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出由胡兰成所撰。就这样,他们的感情有了一个踏实安稳的关系——夫妻。
这一段时间,也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间。胡兰成对她的写作是有帮助的,两人会一起讨论一些文学话题。而张爱玲的散文《爱》,在开头就说,这是一个真的故事。的确是真的故事,是胡兰成的庶母的故事。也许他是给她的创作提供灵感的吧。但,这样的时间,并不长。
时间已经接近了44年年底,时局明显地在变动。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而胡兰成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有了危机感。有一个傍晚,两人在张爱玲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暮色。胡兰成对她说了当下的时局,恐自己将来有难。张爱玲虽对政治不敏感,但此刻,她知道,这个国,这一次是真真连到她的家了。汉乐府中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的句子。而张爱玲此刻是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两句诗的含义。胡兰成说“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是能逃脱这一劫的,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张爱玲笑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就是这样真实的期盼!但两人果真是要分别了! 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有一天,胡兰成在路上遇到了轰炸,人群一片慌乱,他跪倒在铁轨上,以为自己快要炸死了,绝望中,他只喊出两个字:爱玲!这个时候,他还是全心爱着张爱玲的吧。
但胡兰成毕竟是个毫无责任感的人,来武汉不久,他便与汉阳医院一个17岁的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他不向小周隐瞒张爱玲,但又向她表明要娶她——只有做妾了。但小周的生母是妾,她的反应是,不能娘是妾,女儿也是妾。于是胡兰成又进行了一次婚礼,似乎全然忘了张爱玲的存在。而张爱玲对此一无所知。她给他写信来,还向他诉说她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小事。她竟还是那样投入地爱他。
1945年3月,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个多月。此时,他才将小周的事情告诉了张爱玲。她是震动的,因为她把自己对胡兰成的爱看作是那样坚贞不可动摇的,但又怎么会冒出来一个小周?此时,张爱玲的心已被刺伤了,但她仍是爱他的。于是她只有默默承受。两个人在一起,胡兰成倒是再也不提小周了。也许他就是这样一个只看见眼前的人。
可惜,5月,胡兰成又回到了武汉。一见到小周,就有回家的感觉——他又忘了张爱玲了。
时局大乱,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末日也来了,重庆方面定会惩办他这样的汉奸。于是他逃到了浙江,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果是姓张,只是不叫张牵或是张招,住在诸暨斯家。
斯家的儿子斯颂德是胡兰成的高中同窗,胡兰成年轻的时候就曾在斯家客居一年。斯家的男主人已逝,是斯家主母维持生计。斯家还有个庶母,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曾经与斯家老爷生有一女。在这样的乱世中,斯家人安排胡兰成去温州范秀美的娘家避难,由范秀美相送。只这一路,胡兰成就又勾引上了范秀美。未到温州,两人便已做成夫妻,对范家人以及邻居也以夫妻相称。刚离开张爱玲、周训德的胡兰成,此刻又与范秀美在一起,可见他的滥情!
然而,已有半年未曾见面的张爱玲,竟一路寻着来到了温州。这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三角关系,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尴尬。因为怕范秀美的邻居对三人的关系有所猜忌,他们三人都是在旅馆见面的。一个清晨,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隐隐腹痛,他却忍着。等到范秀美来了,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但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就会好的。张爱玲当下就很惆怅,因为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是胡兰成的亲人,而她自己,倒象个“第三者”或是客人了。还有一次,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要给她作画像。这本是张爱玲的拿手戏,范秀美也端坐着让她画,胡兰成在一边看。可刚勾出脸庞,画出眉眼鼻子,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只是一脸凄然。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张爱玲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夫妻像”吧。张爱玲真的是委屈的,她的心里只有这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的心里却装着几个女人,叫她怎么能不感伤?
离开温州的时候,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真是天公应离情。她叹口气道:“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这场雨,也冲刷了他们曾经的“倾城之恋”。张爱玲已经知道,她这一生最美的爱情,已经走到了辛酸的尽头,再有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两人偶有通讯。张爱玲也会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胡兰成,只因怕他在流亡中受苦。
有一次,胡兰成有机会途径上海,在危险之中,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他不但不忏悔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对一些生活细节处理不当。还问她对自己写小周的那篇《武汉记》印象如何,又提起自己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当夜,两人分室而居。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道别,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涟,哽咽中只叫了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在爱情的世界里,张爱玲是软弱的,她一直处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下,似乎总被牵着鼻子走,却不知该如何是好。或者,她明知道这一切不该是这个样子,一个滥情的男人于自己,还有什么值得珍惜的呢?事实上她确是不忍放弃的,即使这个男子三番五次的无视她的自尊。这中被牵制的情感就像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一样,对于情,总难以割舍,抱着一次次的幻想去解释,原谅。
大多女人的天地是狭小的,丈夫,爱人便有可能成为自己生命的全部,就像《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借白流苏的口道出了:“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在那些男人女人的故事里,婚姻总是这样一种难言的苦涩。